
车在盘山路上拧麻花哩,窗户外头,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边边子搅在一搭。山崖崖一层一层的,就像老天爷压下的千层饼。猛地拐过一个山豁豁,嚯!一片翠绿劈头盖脸涌过来——积石山大墩峡到哩。
这名字听起来实诚得很,跟咱西北汉子的性子一样,可里头藏的景致,俊得叫人心尖尖颤哩。站在峡口子上,左手边是种庄稼的熟土,右手边是放牛羊的草山,我就站在这个时光交界的当当里,等着听四季怎么换调调。
当地人说,“墩”这个字,是从山顶上的大墩堡来的。那堡子明朝年间就有了,是看守积石关的烽火墩台。到了清朝咸丰年,一个叫赵桂芳的州官在原墩上修了堡子,起名“静安堡”。西门正对着积石关,门头顶上刻着“积石锁钥”四个字。说得攒劲——大墩峡,可不就是打开咱甘青地区宝匣子的钥匙,也是打开四季轮转的钥匙么!
我顺着新修的木头栈道慢慢走,脚底下水声哗啦啦的,两岸的树绿得要淌下来。你且想不到,三十年前这里还是个秃山梁!两边山上光秃秃的,沟里头就剩下些刺蓬、毛榛榛。在党的阳光照耀下,咱们当地人马学明,带领当地老百姓,一锹土一桶水,硬生生种出了钻天的杨树、柳树、槐树,让丁香花又香遍了山坡坡。现时嘛,人都说这里是“西北的小版纳”,草木多得数不清。人的心劲儿配上老天的成全,在这搭唱了一出攒劲的戏。
日头斜斜地,从树叶缝缝里洒下来,在地上印出晃悠悠的光影影。我美美地吸了一口气——松树皮的清冽、黄土的厚实、泉水的甘甜,还有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、时间焐熟的味道。我知道,我已经踏进四季唱开的歌里头了。这歌,从春天起头。

春:山丹丹红破天
大墩峡的春天,是踩着冰碴子“咔嚓咔嚓”的响声来的。
三月的高原,阴洼洼里雪还赖着不走,可阳坡坡上,土底下已经憋不住哩。最早探头的是那些叫不上名字的草芽芽,从石头缝缝、烂树叶底下,顶出鹅黄的尖尖,羞答答的。接着,山桃、野杏也憋不住哩,黑夜里悄悄鼓胀起粉白的花苞苞。清早进山,一抬头就能叫那一树树的花惊着——在灰塌塌的山崖背景前,这些花开得泼辣又天真,好像把一冬天的力气,全攒到这一回开放上了。
可大墩峡春天真正的“红火”,要等到四月后半哩。那时候,从沟底(1800米)到山顶(3300米),颜色就像火一样从下往上烧。当家的是西北杜鹃,咱本地人叫“山丹丹”或“映山红”。它们不是单蹦蹦地开,是成山成洼地燃哩!从叭口沟到湾架山,再到注洼沟,杜鹃花就像打翻了的红染缸,把山脊、沟壑全淹了。那红,不是江南杜鹃那种水粉粉的红,是叫高原的日头晒透了的正红、朱红、猩红。站在黑大山顶(3300米)往下看,整个峡谷就像晚霞泡透了,又像地心的火喷出来,那种泼天盖地的红,能烙进人眼窝里,也能把心点着。

跟杜鹃争春的,是紫丁香。它们爱长在低些的缓坡上,一丛一丛的,淡紫色的花穗穗像一团团紫烟,香气却浓得化不开,沉甸甸地坠在空气里,能飘几里地。走在丁香棵子里,衣裳头发都是香的,熏得人昏昏然,好像自己也变成春天的一部分了。
春水醒哩。雪水化开,泉眼眼苏醒了,无数丝线样的细流从岩缝里渗出来,汇成溪,叮叮咚咚地唱开了。有名的“瑶路泉”水旺了,清冽冽、甜丝丝的。湾架山那个80多米高的大瀑布,也挣脱了冰壳壳,露出了真威风——水头从崖顶上扑下来,砸在底下的巨石上,溅起半天高的水雾雾。日头从水雾里穿过来,架起一道道小虹,时有时无,跟仙家随手丢的彩桥一样。
人间的活气,也随着春天涨满了。大墩峡东面,就是保安三庄之一的大墩村。春上,保安族的人家忙活开了:男人们拾掇犁耧,准备下种;女人们晾晒冬衣,拆洗被褥。最是那些老人们,爱坐在村口老榆树下,弹起口弦子,漫起“少年”(花儿):
“正月里来是新春,
大墩峡的松柏绿茵茵;
妹妹是牡丹开不败,
哥哥是绿叶托终身……”
歌声随着风,钻进峡谷,跟鸟叫、水响、风声搅在一搭,分不清哪是天生,哪是人唱。可就是这股子交融,让大墩峡的春天有了厚度——它不光是自然的醒来,更是一个族群、一方水土精血魂魄的勃发。
有个春日的早晨,我碰见一位采药的保安族阿爷。他背着个旧背斗,拿个小铲铲,在杜鹃棵子里细细寻找。他说在挖“羌活”,治风湿的药材。“春气上升哩,药性最足。”阿爷说话慢腾腾,眼睛却亮得像鹰。他指着满山的红对我说:“这山丹丹为啥这么红?老古话讲,是大禹爷治水时节,受伤淌的血染红的。”
这话让我心里一震。大墩峡这一带,正是大禹“导河积石”的起头处。禹王泉、禹王洞、禹王石……都在说四千多年前那场惊天动地的工程。要是杜鹃真是禹王的血变的,那这满山遍野的红,就不光是花的俊,更是咱先人创业精神的根苗,是华夏子孙吃苦耐劳的初心。
春末梢上,我爬上静安堡的断墙墙。这咸丰年间修的堡子,如今就剩下些残垣断壁了。可站在这搭,眼界宽着哩:东望黄河像一条金带子,西望峡谷深不见底,南面是大墩村的炊烟袅袅,北面是积石关的威武身影。春风拂在脸上,带着远山雪水的润气,也带着历史深处的叹唱。我想,大墩峡的春天为啥这么抓人?不光为花开得疯,更为它让每个来的人觉着——自然和人,在这搭从来就没分过家。它们一搭里喘气,一搭里在春天醒来,一搭里在光阴里生长。

夏:绿波波漫上天
要是春天的大墩峡像个穿红挂绿的新媳妇,那夏天的大墩峡,就是个精精神神的少年娃。
一进六月,高原的日头毒了起来,可大墩峡却迎来它最舒坦的时节。一进峡谷,一股凉气就扑到身上,跟钻进了天然空调房一样。这凉气从哪来?从遮天蔽日的树荫里来,从年头到年尾不化的雪山水里来,也从这高高低低的海拔自个儿生出来。

夏日的绿,是泼洒开的绿,是绿到不能再绿的绿。华山松、油松、青冈、红桦……各样的树可着劲儿伸枝展叶,在峡谷上头搭起了绿莹莹的穹顶。日头得费老大劲才能从叶子缝里钻过来,落到地上就成了柔柔的光斑斑,风一吹,晃晃悠悠的。栈道两边,灌木长得很繁,蕨类植物的叶子像羽毛一样舒展,苔藓在石头上铺了厚厚一层,绿得发黑,绿得流油。
水,是夏天大墩峡的魂灵。大大小小五条河、二十多处瀑布、数不清的泉眼,这个时节全都到了最旺的时候。水声成了峡谷不变的背景音:近处溪水哗哗,远处瀑布轰轰,再远些还有水雾嘶嘶的声气。闭上眼睛,觉着自个儿漂在一片声音的海里,心头的烦杂,都叫这水声淘洗干净了。
最数湾架瀑布威风。80多米高的水头,夏天水最大的时候,真格像一条白龙从山巅直扑下来。站在观景台上,离着还有百十米,衣裳就叫水雾打潮了。水声震得耳朵嗡嗡的,说话得扯开嗓子喊。那水流砸在底下的巨石上,碎成万千颗银珠子,日头一照,明晃晃的。有时候,风把水雾吹成个弧弧,彩虹就在水雾里生出来,一头扎进深潭,一头挂在悬崖上,梦一样。

可大墩峡的水不光是雄的,更多时候是秀的、柔的。比方那些藏在林子里的小瀑布,才两三米高,水柱细细的,像姑娘家的辫子。再比方一湾又一湾的水潭潭,水清得能一眼看到底,水底的石头子、游动的小鱼儿清清楚楚。走乏了,坐在潭边的石头上,把脚伸进水里,那股子透心的凉,立马能把暑气赶得远远的。
三伏天里,大墩峡成了真正的“天然氧吧”。方圆200公里没有工厂的黑烟烟,空气干净得吸一口都甜丝丝的。兰州、西宁、银川,甚至西安的游客都往这搭跑,他们不光是看景,更是来“洗肺”、来养心的。景区里,常见白头发的老者拄着拐棍慢慢挪,也见年轻父母领着娃娃认花草。每个人脸上,都挂着一种舒展的、美气的笑容。
人气的红火,在夏天展落得最全。大墩村这时候迎来一年里最热闹的光景。保安族的“浪山节”多在夏天。人们穿上压箱底的民族衣裳,带上各色吃食,到草滩滩、林地林里游玩浪山。男人家赛马、射箭、摔跤,女人家则忙活着煮手抓羊肉、蒸麦穗包子、炸馓子、炖盖碗茶……
我有幸浪过一回山节。那是在黄草坪——大墩峡跟前的一片高山草甸。草甸绿油油的,像块巨大的绒毯子,上头开满了杂花。保安族乡亲围坐成一个大圈圈,中间的空地上,年轻后生正在表演打“保安腰刀”。这腰刀有140多年的根底了,是保安人最要紧的手艺。2006年,保安腰刀锻制技艺成了国家级的“非遗”。我看着那个年轻的匠人,光着膀子,汗水在古铜色的脊梁上淌成小河。炉火红堂堂的,锤声叮叮当当,一块寻常的铁片子,在他手底下一锤一锤,慢慢有了刀的形貌。他那专注的眼神,那麻利的动作,不像是在做活,倒像是在完成一场神圣的交代。
最让我忘不掉的,是麦穗包子。这不是寻常包子,是保安人待贵客的顶高礼数。包子的馅馅里,真有麦穗穗——是在麦子灌满浆还绿莹莹的时候掐下来,蒸熟晾干,第二年用时再蒸一遍切碎拌进去。我咬了一口,皮子筋道,羊肉喷香,那麦穗穗呢,带来一种独特的嚼劲和粮食原原本本的甜味。这味道里有日头,有雨水,有一年四季的等待,有一个民族的心思和情义。
天黑了,草甸上点起了篝火。人们手拉手跳起了保安族的“宴席曲”。火光映红了一张张笑脸,歌声在夜空里传得老远老远。我仰头看天,高原的星空清亮得很,银河横跨天穹,星星密得跟沙粒子一样。那一刻,我猛地明白了“浪山”不光是个玩——它是对自然的敬畏,是对生活的热火,是对自己根脉文化的守护和传续。
夏天的大墩峡,还有一些特别的“住户”得记一笔。随着生态环境缓过来了,成群的鸟儿在这搭觅食做窝,鹿、狼也时常露面。
有一天傍晚,我在注洼沟深处,远远看见一只梅花鹿在溪边喝水。它机警地竖起耳朵,可没立马跑开,只是静静地看着我。我们就这么对了眼儿有几秒钟,然后它一转身,轻巧地跳进了林子。那个情景,让我感动了好长时间。人和自然,本来就能这么安然相处么。
离开大墩峡的那个夏夜,我住在景区边上的农家院里。窗外虫鸣唧唧,山风徐徐。主人家是个保安族阿爸,他给我沏了一碗三炮台盖碗茶,指着窗外黑黢黢的峡谷说:“你看,大墩峡睡下了。可它的水还在流,树还在长,山还在喘气。”是啊,夏天的大墩峡,就算睡着了,也满是蓬蓬勃勃的活气。而这活气,既来自老天爷的鬼斧神工,也来自千百年来在这搭生息的人们,对这片土地的黏着、守护和创造。
秋:山沟沟绽斑斓
九月的高原,头一场霜下来,大墩峡的调色盘就彻底打翻了。

秋天的大墩峡,有的游客说“像个熟透的妇人,妖娆又野性”。这话说得俏,可我觉着,它更像一位手艺高超的画师,用最浓最烈的颜色,画完一年里最辉煌的一幅画。
最先感知秋信的,是白桦和红桦。这两种树是大墩峡的门面,特别是红桦,全国都稀罕。西风头一吹,性子急的白桦林就忙忙地换上了金黄的衣裳,红桦呢,则披上了深红或橘红的外套。从半空里的玻璃栈道望下去,那景致能叫人忘了呼吸:红的、黄的、橙的、褐的……各样的暖色搅在一搭,好像整条峡谷都在燃烧。那红,不是春天山丹丹那种鲜亮亮的红,是更深、更厚、更醇的红,像窖藏的老酒,像傍晚的落霞。
你要是十月中来,还能见着一奇景:有些背阴的山坡,白桦
叶子已经落光了,露出银白白的树干,直戳戳指向蓝天;可向阳的山坡上,红桦还守着最后那点绚烂。一阴一阳,一白一红,对比得扎眼,活像一幅巨大的双面绣,一面工工整整,一面洒洒脱脱。

可秋色哪能就这点?青冈的叶子变成古铜色,杨树是明晃晃,槐树是淡金金,各样的灌木有紫红、赭石、暗褐~~走在栈道上,脚底下是厚墩墩的落叶,踩上去沙沙响。日头透过疏朗的树枝照下来,光线叫染成了琥珀色,空气里飘着干爽好闻的草木香。
秋天的水,也变得沉静了。溪流不再像夏天那样吵嚷,放慢了脚步,清冽冽、静幽幽的。瀑布的水量小了,可样子更多了。有的分成几绺,像水晶帘子;有的贴着崖壁慢慢淌,像薄纱。泉水还咕嘟咕嘟冒着,可手一摸,冰得很。禹王泉在这个时节显得格外神秘,水旺旺的,喷涌着含十几种矿物质的泉水。本地人说,这泉水有特别的功效,秋天接上一壶煮茶喝,能润肺止咳哩。
人间的滋味,在秋天换了另一种风味。秋天是收成的季节,大墩村的保安族人家忙着收庄稼、摘果子。玉米棒子金灿灿地挂在房檐下,辣椒串成火红的帘子,核桃、梨儿、苹果堆满了筐篮。空气里满是粮食的香和果子的甜。
这时候,保安族的媳妇们会做一种传统零嘴——果干。把新鲜的苹果、梨切成薄片,铺在苇席上晒。高原的日头亮堂堂、干爆爆的,几天工夫,果片就缩成半透明的薄片片,吃起来韧纠纠的,甜里带酸,是冬天最好的嚼头。我帮一位阿娘晒过果干,她跟我说:“晒果干,最要紧的是看天爷的脸面。‘要连晴,带点小风风。不敢急,一急,果干上就有黑点点,味道也差了。9”这话里头,藏着过日子的大学问:万物都有自己的时辰,人得学会等待。
秋天也是保安族娶媳嫁女的高峰。我参加过一场老规矩的保安族婚礼,那过程就像一台古戏。新郎要骑着马,在亲友们的簇拥下去迎亲。新娘子出门前,要唱“哭嫁歌”,谢爹娘的养育恩,诉离别的不舍情。到了新郎家,有隆重的仪程:撒核桃枣子(寓意早生贵子)、新郎新娘互喂红枣(寓意红红火火)、长辈训话~最热闹的是“闹公婆”,亲朋好友会给公公婆婆脸上抹锅底灰,戴破草帽,让他们倒骑毛驴,惹得全场哈哈大笑。这种热闹,是对新人的祝福,也是对生活艰辛的一种豁达排解。
秋天的夜里,大墩峡会办“赏月诗会”。这本是文人雅士的聚会,如今游客也能凑热闹。在注洼沟的一块平地上,人们围坐一圈,中间燃着篝火。有人吟诵古人写月亮的诗词,有人漫起月亮的“少年”,还有人现编现唱。月亮升起来了,高原的秋月亮得惊人,圆得饱满,亮得晃眼。清辉洒进峡谷,给山峦、树木、溪流都镶上了一道银边边。远处传来几声狼嚎,更添了几分苍凉和神秘。
这样的夜晚,我常想起那些跟大墩峡有牵连的历史人物。最早的是大禹,他“导河积石,至于龙门”,开了华夏治水的先河。
然后是历朝历代守边的将士,他们在静安堡上守着关隘,保着丝路平安。还有那些南来北往的脚户、商人,他们经过临津古渡,把茶叶、丝绸驮上高原,又把皮子、药材带回中原。如今,这些人早化成了土,可他们留下的故事,却像秋天的落叶,一层一层垫厚了这片土地的文化墒情。
有一年深秋,我在大墩峡遇见一位从北京来的画家。他每年秋天都来这搭写生,已经连着来了十年。我问他为啥对这里这么上心,他说:“大墩峡的秋天,有一种悲壮的美。你看这些树,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把所有的精气神都化成了颜色,烧自己一回。这种不留后路的美,在城里头是见不着的。”他翻开写生本,里头全是秋日大墩峡的速写:绚烂的桦树林、宁静的水潭潭、沧桑的古堡堡、劳作的人影影~~每一张都满是感情。
离开大墩峡的时节,我捡了几片红桦叶子。夹在书里,它们成了永久的念想。每次翻开,都能闻到那个秋天的味道:日头的味道,风的味道,果实的味道,还有一丝丝淡淡的、光阴的味道。

冬:冰晶晶的梦世界
当最后一片红叶叶飘落,大墩峡就进入了它最静、也最像梦的时节。
冬天的大墩峡,不是生命的了结,是另一种模样的盛开。有人说,这里迎来了“第二春”,变得“更加诗情画意”。这话一点不假。寒冷在这搭不是破坏王,而是最了不得的艺术家,拿水和空气当材料,造出叫人惊叹的冰雪世界。
走进冬天的大墩峡,头一个感觉是“静”。那种啥声音都没有的静,能听见自己的心跳,能听见雪花落地的“簌簌”声。峡谷两面的悬崖上,一棵棵青松硬气地挺着,树冠上积着厚厚的雪,像戴了一顶顶白绒帽子。白桦、红桦脱了华丽的秋装,露出清瘦的枝干,在雪地的映衬下,线条格外分明。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树,也各有各的姿态,有的枝桠弯弯曲曲像龙,有的端端正正像少女。
可冬天大墩峡真正的奇迹,是“冰”。这搭海拔在1800到3300米之间,冬天冷得嘎嘎的,滴水成冰。景区借着泉水多、气候冷的特点,在自然冰瀑的基础上,又人工造了小一千立方米的冰雪景致。可最抓人心的,还是那些老天爷自个儿的作品。
顺着峡谷,踏上游客栈道往深处走,你就能看见一眼眼山泉冻成了冰,挂在悬崖峭壁上。这些冰挂千姿百态:有的粗得像柱子,从崖顶直垂到地;有的细得像银针,密密地排着;有的像瀑布冻在了半空,还留着奔流的架势;有的像钟乳石,一层叠一层,亮晶晶的。日头照在上头,折射出七彩的光,仿佛走进了水晶宫。
最神奇的是,泉水在冰面底下还在咕咕地流。你把耳朵贴到冰面上,能听见细细的流水声,那是大地的脉跳,是生命在严寒里的坚持。这些水流到峡谷,汇成山涧,在低温下冻成一湾又一湾的小水潭,潭水清得见底,表面结着一层薄冰,冰下的水草还绿莹莹的。
大墩峡有大小瀑布二十多处,到了冬天,它们全变成了冰瀑。湾架瀑布那80多米的落差,此刻成了一堵巨大的冰墙,壮观得很。走近看,冰瀑里头是淡蓝色的,好像把整个夏天的蓝天都存进去了。表面呢,布满了各种纹路:有水流冻住的波浪纹,有风吹出来的羽毛纹,有温度变化裂开的龟背纹。用手摸上去,冰得刺骨,可那种光滑、坚实的质感,叫人心里生出敬畏。

鸡胸瀑到了冬天也变了样。原来像鸡胸脯的瀑布,现在成了一挂巨大的冰帘子,从峭壁上垂下来,底下冻出个冰洞洞。钻进去,抬头看,冰凌子像剑一样倒挂着,透过冰层的光线下,闪着幽蓝的光,跟龙宫一样。
人间的活法,在冬天转到了屋里头,可更加暖和了。大墩村的保安族人家,这时候开始了“猫冬”。火炕烧得烫烫的,一家人围坐在炕桌边,男人们打制保安腰刀,女人们做针线,娃娃们写作业或者听老人讲古。屋里头飘着罐罐茶的香气,那是用黑砖茶、红枣、枸杞、桂圆、冰糖一搭熬出来的,又浓又醇,喝上一碗,浑身都暖了。
冬天也是保安族办“宴席曲”比赛的时节。这是种传统的歌舞,多在婚礼、节日或者冬天农闲时表演。各村各庄都组织队伍,到镇子上比赛。我在腊月里看过一场,那可是真正的民间艺术大荟萃。表演的都是平常种地的农民,穿上鲜艳的民族衣裳,脸上涂着红胭脂,在简单的家什伴奏下,连唱带跳。唱词五花八门:有讲古的《大禹治水》,有唱爱情的《绣荷包》,有说劳动的《收麦场》,还有逗笑的《傻女婿》……虽然保安话听不全懂,可从表演者的眉眼、动作里,你能咂摸出那种朴朴实实的、热火火的、从心底里淌出来的欢乐。

冬至前后,大墩峡景区会办“冰灯节”。工作人员拿天然的冰,雕出各式各样的造型:有宝塔,有宫殿,有动物,有神话人物。到了晚上,冰灯里点上彩灯,整个峡谷就成了童话世界。游客们裹着厚厚的羽绒服,在冰灯中间穿行,娃娃们的笑声在冷空气里显得格外脆亮。最受欢迎的是那组“大禹治水”的冰雕:大禹爷手拿工具,领着百姓开山导河,人物活灵活现,场面大气磅礴。这组冰雕不光是件艺术品,更是对地方根脉文化的传续和弘扬。
我在大墩峡过得最忘不掉的一个冬天,是在2023年地震之后。那年冬天,积石山县遭了6.2级的地震,大墩峡景区的设施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坏,路堵了、景伤了,游客中心、旅游步道、索道和玻璃栈道这些地方伤得重,景区只好关了门。我在地震后一个月来到大墩峡,看见的景象让人心疼:落石满地,栈道断了,一些冰瀑也震塌了。
可我也瞅见了重建的盼头。景区工作人员头一时间清理落石、整修线路、恢复供电,还请来专业机构做安全监测。当地政府紧赶着启动了“大墩峡4A级景区旅游基础设施灾后恢复重建项目”,派人员、出资金、搞设计修核心区域。我碰见了景区当家人马学明,这位当年承包荒山种树的创业者,此刻正带着团队全力修复景区。“从去年起,我们就紧锣密鼓地干哩,一心想让大墩峡恢复往日的风采。”他指着正在拓宽的主游步道说,“这回修,我们还加装了防护网,让游客来得更安心。”
那个冬天,大墩峡的冰雪还是那么好看,可多了一份沉重,也多了一份韧劲。我看见工人们在严寒里施工,他们哈出的气在空气里凝成白雾;我看见村民们自己跑来清理道路,脸冻得红扑扑的,可眼神定定的。一位保安族阿爷跟我说:“大墩峡是我们的家舍,地震能震垮房子,震不垮人心。春天一到,山丹丹照样子开红。”
离开的时候,我在景区门口看见一棵松树。树干在地震里叫落石砸歪了,可它没倒,斜着身子还在长。枝头的积雪在日头下闪闪发光,像戴了一顶王冠。这棵树,不就像大墩峡自己么?不管遭啥磨难,生命总能找着出路,俊模样总能重新绽开。

心:一层层荡开花
几天来,我把大墩峡的四季走了个遍。春天的山丹丹,夏天的绿波波,秋天的五彩林,冬天的水晶宫,每一幅画都深深印在我的心版上。可我越来越觉着,大墩峡的俊,不光在四季分明的景致,更是“心”贯穿始终的人气儿。
这是多民族一搭里过光阴的地方,保安、东乡、回、撒拉、土、汉……好几个民族在这搭生息、和睦相处。民族文化、黄河文化、大禹文化在这搭交融,生出了独特的风景。走在峡谷里,你随时能听见不同的话语、看见不同的穿戴、尝到不同的美食,可它们都指向同一个心心:对自然的敬,对生活的爱,对和美的求。
大墩峡也是一本生态复元的活教材。从三十年前的荒山秃岭,到今天的“西北小版纳”,这个过程真真应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道理。这不光是自然的恢复,更是人和土地关系的修好。人不是自然的征服者,是守护人,是共生者。
站在静安堡的废墟上,我最后一次眺望大墩峡。夕阳西下,给峡谷镀了一层金边边。远处,黄河像一条安静的带子;近处,大墩村的炊烟袅袅升起。四季的影像在我眼前叠化:春的花,夏的绿,秋的红,冬的白。它们不是割裂的碎片,是一首完整的、雄浑的交响。每一个季节都是离不了的乐章,共同奏响生命轮回的壮阔旋律。
而人的故事,就像这交响里的主旋律,时而高亢,时而低沉,可一直贯穿到底。从大禹治水的传说,到守边将士的烽烟,再到今天各民族共建家园的实绩,这条人文的脉线,让大墩峡的俊有了温情、有了柔情、有了亲情。
天色暗下来了,头一颗星星蹦上了天幕。峡谷里亮起了点点灯火,那是民宿、是农家乐,是还在忙活的人们。晚风送过来隐约的“少年”声,调子苍凉又深情:
“大墩峡的四季歌,
说不尽来唱不完;
春有杜鹃夏有泉,
秋叶如金冬冰玉;
最好的景色是人心,
各族儿女共家园……”
是啊,这就是大墩峡的四季歌。它唱的是山河的壮丽,唱的是时光的流转,唱的是生命的韧劲,更唱的,是人与自然的和合共生,是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共美。这首歌,已经唱了千百年,还要接茬唱下去,一直唱到永远。
而我,只是个有福的过客,有幸听到了几个段落。可就这几个段落,也够我用一辈子去回味,去感恩,去传唱了。因为在这歌里,我听见了整个西北大地的呼吸,听见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脉动,听见了人与自然最本真、最美气的相处之道。
大墩峡,谢谢你,用四季的歌曲,教会我怎么在这个纷繁的世上,守住一颗干净又丰盈的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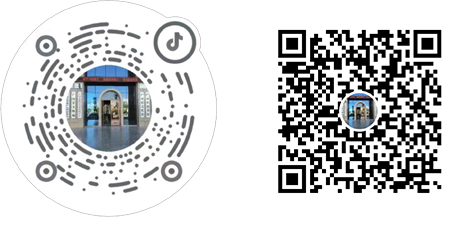
Copyright 2022-2023 临夏广河县文化馆 All Rights Reserved.陇ICP备2022002248号-1
 甘公网安备62292402000120号
甘公网安备62292402000120号